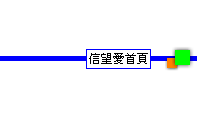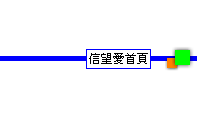車子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好長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再親近這樣的山了。
屬於平地,或屬於城市的我們,擁有太多理由為了這種出走感到欣喜。
同行的僑生朋友對這塊島嶼的印象,也許僅僅限於學校所坐落的工業都市裡
,那些姿態高傲的煙囪和冰冷的水泥大樓罷了。望著友人搖下車窗,驚覺於
原來這片土地也有清新的空氣和壯美的山河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自己上山
的動機,並不是為了受風景的洗禮而來。
有別於僑生朋友,自小就在島嶼上生活的我們,其實是挾著某種程度的
怯生進入山區的。雖然山依然翠綠,雖然沿路上一直有令人驚艷的黃色花叢
;那些整片整片彷彿被巨大的天外之力轟然削去的光禿山壁,以及不尋常的
顛簸道路,都隱隱透露著在這裡,在車輪壓過的痕跡下,在我們目光掃過的
空間裡,曾經發出多麼淒厲的哀豪,或橫陳著令人膽戰心驚的血光和遍野屍
肉。
一路上有怪手正在搶修路面和可能發生落石的山壁。或許需要整修的區
段太多,施工中的警告措施便嫌粗陋了。我們的四輪傳動車,一共三輛,載
著二十多人,陸續險象環生地挨過急急迴旋的工程車體。
「為什麼不插個警告標語?還是反射鏡呢?」
也許,我們對於島嶼境遇的無奈和對掌握處理公共事務者的憤懣已經累
積得過於沉重,過於巨大。從來,對環境的批評幾乎成為國民對環境施予關
心的必然態度,而當國家面對如此難以預警的破壞時,習於無奈的島民自然
也只能更加理所當然地發洩對救災措施的不滿了。
不知是怎樣的巧合,車上大家竟一唱一搭地比較起自己的國家和理想中
的夢幻烏扥邦。
是僑生朋友的一時感慨吧,
「我們那裡真的像天堂呢,這裡的房子看起來都好像墳墓。」
猶是同樣一鼓龐大的無力感,使得大家的談話裡似乎一再證明了一個事
實:幾百年前被異邦探險者稱呼為福爾摩沙的美麗之島,再也無法挖掘出可
以令島民能驕傲地生存下去的元素了。
這當下,我寧可保持緘默,卻也發覺有一股極欲為島嶼辯護的熱度湧上
心頭,令人心酸、胃痛,欲喊無聲。
我們是以「醫療團」的身分上山的。兼當司機的傳教說,有一股使命驅
使著他,在將來,還要到許多偏遠的第三世界國家傳福音,像不丹、尼泊爾。
有時候我們真難解釋這些困惑。當我們願意奉獻一己之力到需要援助的
地方幫忙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羨慕起許多有良善制度的國度,以為那裡才
是我們生活環境的模範典型。
「為什麼大家不乾脆低頭下來為這片土地禱告呢?」在一片熱烈的討論
與對自己的家園的韃伐聲中,我默想著,試圖理出「奉獻、形式、距離」等
等之間可能存在的種種矛盾。
地震過後,國人對自己的鄉土的愛恨情愫,顯然更複雜許多。當車子行
經一棟傾斜的大樓,我暗暗地想,當時這樓房如果那麼乾脆地倒塌了,如果
這棟樓是一間有住人的公寓,如過住在裡面的是我的家人,甚至是我;許多
情緒,也許就不一樣了。
誠然,我們是不可能將災民恐懼或憤怒移植在自己的心裡面的。地震那
天天剛亮時,南台灣的太陽、汽車、人,都還是同一個樣子。我們每天每天
地依同樣的頻率過活,中午在自助餐店裡吹著冷氣,看電視新聞裡報導的死
傷人數不斷攀升,偶而眉頭一皺,或感同身受似地喟嘆一聲,或捐了一點零
用金和睡袋。也許哪一天看到報紙上有個「地震後優惠再優惠專案----移民
」,便決定一勞永逸地揮別了家鄉。
一走了之,突然成為一件多麼輕而易舉的事。然而,這些在同樣一片土
地上揮汗,卻無法擁有等同的社會地位或具備扭轉生存條件能力的災民又何
去何從呢?
我們終於來到了南投縣信義鄉裡的布農部落。有一次聽一位布農醫生作
家說,他們的家鄉是不怕土石流的,因為祖先曾經告訴他們,石頭在玩耍的
地方,就不適合人去玩耍。
想來,這些原住民部落的傳說故事和還真切實際。只是這回,他們再也
無法以這種常識來應付如末日般的天搖地變。
而這些原本就一代一代根植於此的原住民們,能有的措施,便不是祇有
一走了之那麼簡單了罷?
來部落之前收到了學姊寄的電子信件,學姊的語氣沉重,帶有控訴語氣。
「政府說他們的房子是蓋在國有地上,所以沒有任何的補助,鋃行也不
會貸款給他們,因為他們沒有『自已的』土地,國有地上的房子根本不能辦
貸款;雪上加霜的是,長老教會的木屋補助,不知何故落空了........對於
他們這樣的情況,我心裡真是非常地難過,地震後家園己毀,本來經濟情況
已經夠差了,結果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這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早在幾百年前,當高山族被大漢沙文主義逼得
走投無路之下退守山區,卻無料山區也被霸道的法規定為國有土地。我們能
擁有像違建卻不是違建的橫貫公路或產業道路,原住民的房子卻註定要成為
無辜的違章建築。過去,一向被稱為「同胞」的族群,到頭來只又在名稱上
被表示了善意。
而這次上山,我卻驚覺原住民朋友的勇氣。
推土機、怪手、水泥車嘎吱的工作著。這些回鄉重建家園的青年,大多
是請了假或辭了工作回來的。
教會的詩班高唱著「一生一世的孩子回家吧」,似乎跟現況有著巧合的
呼應。只是,我們猶難想像,當他們辭了工作,失去了平日用來維持生計的
薪水之後,等房子、學校建好了,帳棚一一拆下,居民重回原以為之失望的
教會時,村民還有多少能耐重新找工作,而隨即到來的冬天又要帶給他們多
少苦難?
學童一一放學回家了。聽到了我們的廣播,他們陸陸續續集中到臨時搭
起的教會聚會廣場。我們深深了解,只有單單派出一次兩次的醫療團,根本
無法為當地帶去多麼具有實質意義的幫助。義診所能提供的療傷,也只限於
一些不用依賴藥物就能痊癒的感冒或外傷而已。而大學生用心策劃的主日學
活動,除了為當地的學童帶來能喚起一時新奇與欣喜的遊戲和禮物,我們也
只能夠承認學童的命運大致上還是依照這樣的模式進行著:能適應體制的就
離鄉,其餘的留下,終其一生在原鄉奮鬥。
而這些去留的禍福,就更難詮釋了。
望著這些毫無心機的原住民兒童熱烈著搶答著大哥哥大姊姊設計的有獎
徵答,「耶穌為什麼可以拯救眾人?」「上帝為什麼是萬能的?」我們如何
能透視出這些純真的笑容的背後所隱藏著的我們永遠無法體察的悲慘命運?
從更高一點的山上走下來,目睹崩毀的教會和常常的地裂,同行的泰雅朋友
不禁嘆息:「上帝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一瞬間,我們一路上來的責難似乎更顯得無解。平日我們多希望自己生
存其上的島嶼上能開出美麗的花朵,長久被曲解的歷史記憶和民族意識卻逼
使我們失去維持樂觀的權利。而當我們乾脆麻木地享受著本質也許是災難的
經濟奇蹟或社會假性的公平正義時,有一群人,還必須樂天的生活在這裡,
靠著祖靈的庇祐、上帝的保守,一生一世的守著早已被剝奪的土地。
教會座落在部落的頂端,我們很訝異這些部落雖然都只有幾百幾千人,
卻能組的出極為優秀的唱詩班。這也許是上天賜給原住民的恩惠,若不是他
們的內斂,這樣的合唱團在城市裡真算得上是職業水準的歌者呢。這使我想
起在一次電視新聞裡,看到一位行政首長出席原住民青少年的聚會。這位「
長官」還是用他令人熟悉的氣魄豎起大拇指對大家說:「原住民朋友們只要
努力,也會出頭天。像阿妹,像陳義信......」
或許我們仍無法責怪這位長官短淺的觀念,畢竟他們已經很努力在政策
上張揚「公義」了。然而,我們知道,只要一天這些只能迎合淺薄文化的表
面功夫益發華麗,我們的朋友就要漸漸忘了原來擁有強壯的小腿肚,能上山
打獵,當一名勇士,才是族人的榮耀和尊嚴所在。
幾個孩子們在我們這群不速之客面前,依然毫無顧忌地打打鬧鬧起來,
在地上翻滾,弄得全身骯髒,好像這樣的玩法多麼理所當然;換成是我們小
時後,也許又要回家挨罵了。
「抱我,抱我!」他們這樣叫嚷著。從我們得到訪,到我們回去時,這
些孩子彷彿早已與大家熟識了一樣,竟絲毫看不出他們的陌生與怯懦。在他
們的眼中,所謂「人」,應該是一種最自然,最純真的個體。
天黑的時候,部落異常寂靜。也許厭惡了城市的喧囂,晚風、小米酒香
和山霧頓然成為一種恩賜。招待我們民宿的主人說,房門不用鎖,他們的大
門已經好幾年沒有關了。
於是我們也很自然的走出戶外。以為會有星星,霧卻很濃。在部落底下
遇見了一個小時以前還和大家玩的正樂的布農青年。他正在當兵,隔日就要
收假了。我們問他這麼晚要去哪裡?他說難得回來,要找朋友聊天。
這裡就是他們的家,那種感覺很強烈。對於「家」,我們或許感到不足
為奇,在城市裡我們累了餓了便回家,換了工作就再搬到另一個城市,在那
裡我們還會有新家。
這樣一生註定在此落腳的族人,就沒有理由和能耐因為生存條件的日趨
單薄而選擇了不歸之路。
教會的裝飾燈正閃著,在寂靜幽暗的部落裡顯得特別溫馨。雖然,主體
建築正在補強,裡頭用了層層疊起的竹竿支撐著,我們卻知道這是當地賴以
繼續生存下去的主要資源之一。
下山的時候,我們都筋疲力盡了;但我們卻知道,當我們的車子駛離部
落,對於我們自己,以及永遠無法和山上的土地割離的村民,都開始有了另
一種更深切的抑鬱和責任在發生。
我們的記憶裡,除了當地傳道人的淚水,和詩班在辛酸的遭遇之下仍然
勇敢而堅定聊亮的歌聲外,該有的,應該不只限於難過和從來即有的無奈而
已。
當當地的接待滿懷愧疚地說等下次重建完了我們再去時再好好招待大家
的同時,我們何忍去接受這種何辜的歉意?
一聲聲道別時喊出的加油,究竟能帶給村民多少力量,已經不是那麼必
要被估算的了。然而我們都盼望著,當下次有緣再見時,詩班的歌聲猶然嘹
喨,而且不再只有在苦難中唱出勇敢,還有歡笑,還能為豐收的好日子謳歌。
(本文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二年級學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教會、校園福音團契高醫團契會友)